“描述一段历史,中间自然会有沉重的部分,有悲剧的气息,有沧桑的巨变,但是所有的沧桑,我都是用一种‘含泪带笑’的方式来处理的,一些很严肃的话题,我也希望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态度来面对,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,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它。”
作者 | 段志飞
编辑 | 程迟
题图 | 叶兆言
对大多数读者来说,一个享誉数十年的著名作家,他的年龄总是备受关注。
两年前,65岁的叶兆言,说自己在写长篇小说《仪凤之门》时,就已经抱着“可能是最后一部”的心态在写作了。然而,读者倘若信了这句话,怕是要陷入关爱“老作家”的误区。
在文学圈,叶兆言被大家认为很“卷”,无论是花在写作上的时间精力,还是最后的作品产出,都相当惊人。他的年龄越来越大,工作时间却在增加,一年365天,他每天坚持写作,从未间断。
11月中旬,叶兆言带着他的长篇小说新作《璩家花园》来到深圳、广州的两场分享会。参加活动也不会打乱他的“计划”——他知道记者上午10点会到,于是早上5点多在宾馆起床,一直写作到8点30分,再出门吃个早餐,在附近锻炼闲逛一圈,然后准时回来。
《璩家花园》
叶兆言 著
译林出版社,2024-9
在接受《新周刊》记者采访时,叶兆言说,作家无所谓退不退休,反倒是时间越来越珍贵:“我每天做好规划,就是想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写作,如果时间不够,就用勤快来弥补。”他诚恳地表示,写完《璩家花园》之后,能够顺利出版是意外惊喜:“到了我这个年纪,还能自由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,并且让读者看到,也算是种奢侈。”
叶兆言书写南京四十余载,堪称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“文学代言人”。无论是《艳歌》、《夜泊秦淮》、“秦淮三部曲”,还是《南京传》《仪凤之门》,无不是从沧桑变迁中追索历史文化的作品。
新作《璩家花园》的故事依然发生在南京,不过用叶兆言的话说,这部小说中有太多他自己的记忆,“不仅是关于南京的故事,更是关乎人与时代关系的故事”。说起时代,不禁让人想起他与父亲叶至诚、祖父叶圣陶,祖孙三代人一起投身于中国文化百年事业的壮举,在整个文化界都实属罕见。
采访期间,叶兆言很放松,聊着记忆里的父亲和祖父,说如今自己也成了“老家伙”。他偶尔走神,想着已经错过的NBA常规赛下半场直播,对力量和速度依然向往。他偶尔又聊到喝酒,说“能写犹如能喝,能写就已经很知足了”。分别的时候,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子,说下午打算去游个泳。
以下是《新周刊》与叶兆言的访谈整理。
用“含泪带笑”的方式,
重拾历史的沉重
《新周刊》:这部《璩家花园》是你现有的14部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大、故事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,为什么想写这样一个故事?
叶兆言:很多人以为我只写民国时期的南京,其实我一直想写当代生活,现在终于写出来了。
《璩家花园》讲的是共和国七十余载中的三代人在南京的生活轨迹,里面大量运用了我的直接经验。比如恢复高考、对外开放、下海经商、国企改革,等等,以及主人公与一众亲朋好友的生活变迁和命运流转,很多都是我身边发生的往事。
(图/受访者提供)
写作的时候,那些人就好像在我眼前。我通过“写”走近他们,他们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,如果我不去写,就没有人会知道。
《新周刊》:和很多跨越时代、拥有时间厚度的作品一样,读者读这类小说,都避免不了在心中产生一种难以释怀的郁结情绪,没那么轻松。在读者看来,你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一部平民视角的《南京传》。写的时候轻松吗?
叶兆言:我一直想写一本像契诃夫戏剧《海鸥》那样的作品,有轻松的一面,也有可笑的一面。
描述一段历史,中间自然会有沉重的部分,有悲剧的气息,有沧桑的巨变,但是所有的沧桑,我都是用一种“含泪带笑”的方式来处理的,一些很严肃的话题,我也希望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态度来面对,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,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它。
过去评价钱锺书的《围城》时有这样一句话,“用喜剧的气氛来反映一种悲剧意识”,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完我的作品之后会觉得心情沉重,因为历史中隐痛的部分是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的,我老老实实地把它呈现出来,即使不做是非判断,读者也能自行体会。
(图/《围城》)
《新周刊》:面对历史,有个很现实的问题:这种情绪一旦产生,我们要如何解决呢?
叶兆言:关于如何面对历史,我觉得叙述得最好的是巴金先生,他虽然深受历史的迫害,但是仍然能从反思的角度去谈问题。当每个人都在抱怨集体伤痛,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,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反思自己的历史,“我明明没有罪,但是我觉得自己有罪”,这是我觉得最悲哀的地方。
所以我在《璩家花园》中写费教授的时候,我不是从他被迫害的角度写,而是以一种可笑、狼狈的方式在叙述,其实就是喜剧。这很真实,人物在特定场景里的任何反应,都很难凭空捏造出来,阅读产生情绪恰好说明了我们与历史产生了共鸣。
当然,沉重里面也有一种“隐喻”,那就是在叙述历史这件事情上,下一代总是不比上一代人更重视。费教授会把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录在日记里:到了民有这一代,他所幸还有记录历史的愿望,只不过记录的都是个人的趣味;而到了天井这一代,就已经没有记录历史的意识了,只有当别人讲述他们这一代,历史才会浮现出来——写《璩家花园》就是把这些快要消失的历史重新拾起来。可能以后叙述历史的事情,就只能交给读者了。
人都是被时代塑造出来的
《新周刊》:如果你的记录更多是来自几十年的个人生活经验,那你是如何跳出主观意识,来保证历史的“真实”呢?
叶兆言:我在写作这一部分历史故事的时候,认真考虑过我笔下人物的岁数问题,哪怕是差一岁,人的命运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比如天井一定要出生在1954年,因为这一年在南京历史上很特别,像王安忆、许子东那些上海的知青,在这个时候都下乡了,但是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这届学生,只要不是留级,基本上都留在了城市里。这样的话,天井的经验,其实就是代入了我的经验,这是在我认知范围内的真实,不可能凭空捏造。
(图/《乔家的儿女》)
除了我的个人生活经验,也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现代文学有关系。我过去很喜欢看像费教授那个年代人写的日记,也喜欢看年谱。日记可能会有主观、自恋、作假的成分,但是比小说更真实。
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(1959-1961),老百姓很多都食不果腹,但是在高级知识分子眼里,看到别人吃东西就会形容像“饿狼”一样,甚至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得意的成分。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就是会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,这些都是我从他们的日记中见到的,非常真实。
《新周刊》:“璩家花园”这个地点是真实存在的吗,还是只是一个文化符号?
叶兆言:地点完全是虚构的,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已经消失了。因为我看过太多老街区的消失和新文化街区的打造,所以感受很深。这种“改造”中间一定有得利者,也一定有倒霉的人,比如拆迁拆到你这儿就不动了,但是你仍然是街区的一部分,供游客参观。
不光是中国,全世界都这样,比方说我去过的威尼斯,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,可一旦往深处走就会完全不一样。尤其对于那些原住民来说,住在文化街区是件相当令人困扰的事,因为只要是旅游地,就会是一片嘈杂,不适合居住。
(图/《乔家的儿女》)
小说里的主人公天井,从小在这样的街区里长大,乘着历史的巨轮,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,结果命运弄人,兜兜转转一圈又从居民楼里狼狈地搬回到这里,他这才发现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变,老屋改造中特意安装的马桶,是他和阿四老年生活最后的体面。
我想表达的是,其实人都是被时代给塑造出来的,并不完全真实。假如有一天发生战争,光是断水断电,就能让我们的生活回到原点,根本无法想象。这个时候,璩家花园就好比是一面镜子,让我们重新审视“历史的进退”。
《新周刊》:你在后记里提到自己有写得“特别爽”和“特别忧伤”的时候,可以展开分享一下吗?
叶兆言:“爽”很好理解,就是写爽了,就像费教授写的日记,把历史写了下来,是一种记录的爽,但同时很悲哀的是,最后写了又跟没写一样。我确实会有一些联想,觉得自己的小说,也可能是与之完全相同的命运。
“忧伤”来自生命所面对的无力与悲痛。我写天井从来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,当然也会想到我自己的经历,我虽然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,但是我们的语言没办法正常交流,这是非常糟糕的。
(图/《乔家的儿女》)
还有,我在写民有和继女分离的时候也非常难受。这一段让我想起了自己女儿出生那天,等在手术室外看到的一幕: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,挺着大肚子在那儿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,旁边有人议论“等孩子出生以后就会送给别人”。在小说里,继女的命运和生育权同样被他人操控着,身不由己的民有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,只能愧疚终生。
亲情是一场关于“爱”的修行
《新周刊》:你的悲伤,似乎更多来自现实中亲情带给你的体验。你的父亲叶至诚,以及祖父叶圣陶,都是中国文学界的元老和泰斗,如果探讨亲情与写作的关系,读者可能会更好奇,他们对你的写作这件事有什么看法,对你有没有影响。
叶兆言:我觉得没什么影响。他们都不是职业作家,我父亲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戏剧上,我祖父可能更广泛,他还是教育家、文学出版家以及社会活动家。在他们看来,写作可能不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,所以也从来没有暗示过我写作,不鼓励,当然也谈不上反对。我们家庭的传统,其实也是“五四”的传统,就是绝不干涉孩子的自由。
(图/《黄金时代》)
我祖父“听过”我的短篇小说,我的小说发表的时候,他的眼睛已经不好用了,于是就让我堂哥念给他听,他听完之后用苏州话说“不错不错”,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爱和鼓励。
至于父亲,其实他内心是热爱写作的,从小就是一副要当作家的样子,高中也不念了,要去做文学青年,只不过他几乎没怎么出过书,想得太多,干得太少。后来看到我出书了,而且越来越多,他的内心应该是挺复杂的。我现在想起来,自己其实有点残忍。不过他要是还在世的话,看到我现在的状态,他肯定是高兴的,这毋庸置疑。
《新周刊》:你父亲的性格,跟天井的父亲民有挺像的。“遗憾”就好像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情绪,只不过各有各的遗憾。你在后记中还提到想把《璩家花园》这本书留给你的女儿。这也跟“遗憾”有关吗?
叶兆言: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件事了。因为我并没有希望通过这本书创造出什么纪录,好留给自己的女儿,而是像费教授的日记一样,如果有一天没有人能看到它,那我就把它托付给我最信任的人。
(图/《黄金时代》)
总而言之,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,毫无顾忌地把我想写的东西写下来了,最后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,能够顺利出版并且被读者看到,算是意外惊喜,很奢侈。
《新周刊》:婚姻关系也是亲情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种,而且在《璩家花园》中占有很大的篇幅,甚至构成了三代人、好几个家庭之间的牵绊和纠葛。想问你一个跟现代社会相关的问题:在你看来,过去的婚姻和当代婚姻相比较,哪一种更加不容易?
叶兆言:首先我认为全球化一定是好的,自从我们的年轻人恋爱越来越自由之后,我觉得自由恋爱是对的,但我们也并不是非要确定某一种“婚恋观”就一定是正确的。我祖父就是包办婚姻,他们结婚以前都没见过面,但是后来也过得很幸福。
我认为婚姻最大的不幸是“没有爱情”,很多人结了婚之后,爱就消失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的爱更容易消失。当然,这是另一回事。总之,最理想的婚姻还是要有“爱”,不论是过去的包办婚姻,还是现在的相亲,自由恋爱也好,同居也好,都不重要,这些都是由时代决定的。
(图/《小巷人家》)
如果再展开来说,还有现在的年轻人结了婚不愿意生孩子的情况,我觉得也没有问题。很多上一代的老人想看一看第三代,有“弄孙之情”,这很正常,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,但是理智告诉我们,如果婚姻是为了生育,而不是因为爱,这样的婚姻注定很难幸福。
所以婚姻也好,亲情也罢,都是一场修行,关键就在于守护“爱”这件事,其实任何时候都不容易。
校对:河晏;运营:嘻嘻;排版:方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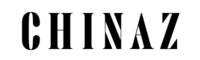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 鲁ICP备2023038971号
鲁ICP备2023038971号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